漱石:文豪消失的童年和母愛
2009/07/01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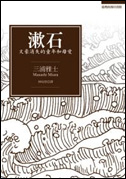 日本一代大文豪說不出口的疑問:母愛真的存在嗎?
日本一代大文豪說不出口的疑問:母愛真的存在嗎?
文豪夏目漱石,和愛因斯坦一樣,死後大腦仍被完整的保存。與森鷗外齊名,同為日本近代文學大家。以《我是貓》、《少爺》等作品廣為臺灣讀者所知,作家生涯一帆風順。一九八四年,他的頭像被印在日幣千元紙鈔上。
這些都是大眾所熟悉的漱石。
然而幼年時期接連更換兩個寄養家庭的過往,讓文豪困擾並懷抱終生的疑惑:「媽媽到底愛不愛我?」這種對母愛感到懷疑的心態,甚至延伸到了對人的不信任與猜忌的態度上。從《我是貓》、《少爺》等作品到後來的《明暗》,背後隱藏的其實是對自身價值的重重疑問;究竟在漱石人生的終點,是否已經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?
作者簡介
三浦雅士 Masashi Miura
1946年生於日本青森縣,編輯、文學評論家、舞蹈研究者。1969年曾進入當時日本知名出版社青土社任職,並參與文藝刊物《Eureka》的創刊計畫。對於文藝界的活動十分熱心參與,三浦為日本文化廳文化審議會的委員,也是日本文藝家協會的理事之一;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,目前在新書館擔任主編,他同時也是立教大學文學研究所的特約教授,持續在每日新聞上發表書評。
三浦雅士為知名的文學評論家,曾擔任多項文學賞的評選人,並對日本近現代文學常有獨特角度的評價。著作豐富同時獲獎無數:《憂鬱的水脈》(獲SUNTORY學藝賞)、《所謂小說的殖民地》(獲藤村紀念歷程賞)、《身體的零度》(獲讀賣文學賞)、《青春的終點》(獲藝術選獎文部科學大臣賞、伊藤整文學賞)、《村上春樹和柴田元幸的另一個美國》、《出生的祕密》、《漱石—文豪消失的童年與母愛》等多本。
其中《漱石—文豪消失的童年與母愛》為三浦雅士以「漱石懷疑母親對自己的愛」為中心,剖析漱石作品人物間的交流與癖性,進而分析作品中透露出的漱石心態。
譯者簡介
林皎碧
出生於台北縣新莊市,臺灣淡江大學東語系畢業,日本國立東北大學文學碩士,專攻日本近代文學,以其專業多次在報章上發表研究報告和隨筆,〈為消逝的日本沉重嘆息〉、〈淺井忠與《湯島聖堂大成殿》〉、〈永不過時的美學精神:《達文西的筆記本》〉等多篇。譯著有《日本名畫散步》、《沙門空海之唐國鬼宴》卷一、卷二、《避暑地的貓》、《不可思議的金錢》、《春之夢》、《夢見街》、《不可思議的金錢》。
章節目錄
第一章 不被母親喜愛的孩子──《少爺》
第二章 棄兒會考慮自殺──《我是貓》
第三章 拒絕上學者的孤獨──《木屑錄》和《文學論》
第四章 處罰母親──《草枕》和《虞美人草》
第五章 逃離母親──《三四郎》《從今而後》《門》
第六章 被母親處罰──《過了彼岸》
第七章 面對面的困難──《行人》和《心》
第八章 孤獨的意義──《道草》
第九章 承認的鬥爭──《明暗》
後 記
作者後記
在人類的歷史裡,不被母親所喜愛的孩子並非罕見啊!何以漱石特別要去面對這個問題呢?為何得和這個問題格鬥呢?對於這些問題,社會變化應該是第一個理由,然而不被母親所喜愛孩子的主題,不只是近代文學特有。這個問題,並非單純因近代家族的形成而產生。這種事,譬如民間故事中的繼母、繼子的主題並非罕見,神話中也有不被母親所喜愛孩子的故事廣為流傳於世界各角落,這些都是很明顯的。
當然,不被母親所喜愛孩子的主題,曾經是公共議題,不過從某一階段就被看成私人的問題。譬如家族、親族、部族,在以血緣為基盤的社會裡,所謂被母親喜愛、不被母親喜愛的主題,某種程度上屬於公共議題。若是移到以別種事物為基盤的社會裡,公私的區分法就變成在滑坡上移動。
漱石的小說被廣為閱讀,這種公私的區分法就會被質疑。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屬於公共問題,戀愛、結婚、家族屬於私人問題,雖然這是一般人的想法,毋寧說正好相反吧!難道「公」不正好就是「私」?「私」不正好就是「公」嗎?譬如驅使人從事革命、政治、戰爭,未必是公的思想或理論。往往是私人的感情。這種私人的感情,屢屢可以回溯到幼年時期所受的屈辱體驗,大抵是其背後受屈辱的母子關係或戀愛關係,因此產生而潛藏在內心的癖性。
許多的小說和電影都是如此設定,而且令讀者、觀眾感動,這顯示公私逆說,對人來說是一種根源性的東西。甚至令人覺得所謂主體性,難道不就是公私逆說嗎?從徂徠到漱石的這一個文脈上,不是有必然性的展開嗎?在《過了彼岸》中,松本把市藏的乖僻和漱石本身的〈現代日本的開化〉的問題重疊,暗示漱石本身也有如此的想法。對《從今而後》中的代助而言,對三千代的戀情既自然也是天命。
反正,不被母親所喜愛孩子的主題,不可能是私人的問題、個人的問題。為什麼呢?因為每一個孩子都有母親,任何人都是由母親生下來。雖然愛這種感情是很清楚,想讓他人完全接受幾乎是不可能。因此,原理上誰都有可能成為不被母親所喜愛的孩子。懷疑自已是否不被母親所喜愛的孩子的心癖,原理上誰都有可能。因為有可能,在內心深處誰都會受傷害、也會去傷害別人。
漱石是否不被母親所喜愛,只有問漱石本身才知道,可是卻辦不到。把自己的心路歷程誠實寫出來就好,對於自己是多麼不了解自己而感到驚訝!寫下這些的是二十九歲的漱石、熊本第五高等學校當教授的漱石。總之,這是漱石本身對於漱石一無所知的告白。因此,才會終其一生持續探索。因此,死後眾多的漱石論只有持續探索。總而言之,如同漱石對自己本身不了解般,至今仍是一個謎團。以謎團般地活下去。不只漱石如此而已。任何人都是如此。毋寧說這正是所謂文學的基本構造。
閱讀漱石,最令人驚訝莫過於探索這個謎團之徹底。
漱石逝世於一九一六年、也就是大正五年十二月九日,從那一年元旦開始連載《點頭錄》。《明暗》則是從五月二十六日開始。雖然《點頭錄》的連載很短,卻在《明暗》執筆之前,從這裡我們知道漱石到底在想什麼?就是第一回文章中「又到正月了」。
又到正月了,回顧過去宛如一場夢,不知不覺中已進入這年歲了,真是不可思議!──開頭如此寫著。接著又寫著;過去只是一場夢。不過是一個假象。若是如此,現在不也是假象嗎?然而,令人驚訝的是天地所覆蓋的當下卻是千真萬確。對於生命的這兩種看法,毫無矛盾地同時並存,有關超越一般理論的異樣現象,自己現在一點也不打算說明。
作為新年用文章,這有些破例。曾經為這般的文章可以上元旦報紙版面而感動。甚至還認為難道現代文明,只是把人弄得淺薄而已嗎?
現在正是最不可理解的事──十九世紀的某思想家所說。這和漱石所敘述一樣。死者可以看到人,生者可以看到鬼怪──另一位思想家所說,這好像在詮釋漱石所敘述的事。
所謂人,就是一個異樣現象。這是漱石所確信的事。自己這種東西,其實就是一個異樣現象。
小學生輕率就自殺,因為認為縱使自殺,所謂自己的現象依然持續。不只是小學生而已。這是人實際的感覺。認為自己會歸於無,這個思考方式確實是人為的,只有人為才會說出如此賢達的話。
謎團的探索,從《我是貓》到《明暗》,一成未變地持續。所謂我的現象,在結構上屬於永遠。說起來,卻是脫離現實。儘管如此,人還是為現實所束縛。《明暗》正在書寫中,如此的思想正在?石的腦中盤旋吧!
自己是否不被母親所喜愛呢?這小小的懷疑砂礫,雖然傷害母貝,還是成為大顆真珠,吸引讀者、引人深深思索。可以認為?石的教科書就是這如此產生。現在還讓人在思考......不,現在不得不更加深思。
 我要協談
我要協談